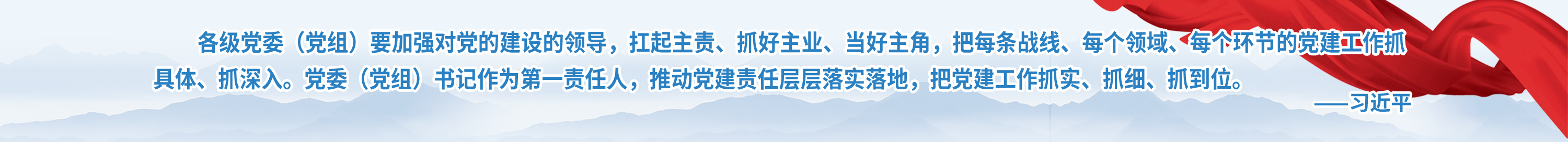文学与新闻协奏爱国乐章

1951年初,萧乾在湖南省岳阳县参加土地改革,写下《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等新闻特写。图为萧乾拍摄的筻口乡土地改革实况(萧乾文学馆供图)
从北京贫苦家庭的遗腹子,到领民国文艺风气之先的《大公报·文艺》主编,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唯一一位中国内地记者,之后放弃英国剑桥大学抛出的热情橄榄枝,追随青年时代的爱国信仰,毅然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新时期以来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为中国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并在耄耋之年把才华再次倾注于翻译,与他的爱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文洁若联手,让号称最难懂“天书”的意识流巨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一批重要外国名著进入华语阅读圈。他,就是萧乾,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新闻报道的重要标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生后半段成为汉译小说史上的一个传奇。特殊时代的苦难,并没有折损他的勤奋与善良,百万字著作之外,萧乾一生勤奋、严谨、热情,他无私奉献、赤诚报国的家国情怀,是他留给我们后辈的一份宝贵遗产。
京派后起之秀的文艺探索
萧乾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1933年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曾协助埃德加·斯诺编选《活的中国》。1935年,他以《书评研究》顺利毕业,同年出版毕业论文,该文在中国书评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之后,他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公报·文艺》,兼任旅行记者。萧乾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是他文学意趣勃发的最初时期。他最早创作的小说《梨皮》发表于1929年,此后发表两部短篇小说集《篱下集》(1936)和《栗子》(1936)、长篇小说《梦之谷》(1937-1938),和短篇小说《一只受了伤的猎犬》(1938年)。1947年以后零星写出《珍珠米》等短篇小说。尽管数量不多,萧乾的小说还是以浓烈的情感表达、深厚的底层关怀、诗意的意境营造等成为京派小说的重要代表。
作为京派文学的后起之秀,他与林徽因、朱光潜、梁宗岱、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来往密切。萧乾结识的文学前辈,尤其是沈从文、巴金、冰心等,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视他为乾弟,不仅帮助萧乾发表崭露头角的小说《蚕》,还与杨振声联合推荐他进入《大公报》,力推萧乾接任《大公报·文艺》主编,并与他联名出版《废邮存底》,频繁的书信交流中充溢着文学的探讨与鼓励;“挚友、益友和畏友”(萧乾写给巴金的同名回忆散文)巴金称萧乾为“奇才”并时时给予他精神上的引导与支持;冰心亲切地称他为“小饼干”(萧乾原名萧秉乾,取谐音),并说“见了‘饼干’,就像见了我亲弟弟一样”。萧乾与巴金、冰心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贵友谊,当事人的深情回忆可见于文洁若的《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和萧乾、文洁若的《冰心与萧乾》两书。
萧乾的童年处于中国在帝国主义铁蹄下苟延残喘的时期,他作品中个人命运的悲歌无不折射着国家地位的没落。作为“暮生儿”的他幼时与母亲相依为命,11岁痛失母亲,开始独自闯荡。他奔波在地毯作坊、羊奶厂和书店,在教会学校崇实学校里半工半读。萧乾小说中“压迫/被压迫”二元对立的情境设置就是他年少时成长经历的折射。受教会学校就读经历和幼年接触的基督教徒的影响,萧乾往往将小说中的压迫者塑造为一些有钱人,或“洋人”“牧师”“传教士”,由此也获得“反基督教作家”的称号。他小说中的被压迫者多为儿童、寡母,以及一些城市下层平民如《花子与老黄》中的“老黄”、《邓山东》中的“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中的“秃刘”等,这些人物共同组成弱国子民的人物群像。萧乾自视为“边缘人”,不时化身为《梨皮》中的“狗儿”、《小蒋》中的“小蒋”、《花子与老黄》中的“七少爷”、《邓山东》中的“我”、《俘虏》中的“铁柱儿”“荔子”、《篱下》中的“环哥”、《放逐》中的“坠儿”、《矮檐》中的“乐子”、《落日》中的“乐子”等贫弱儿童,反复咀嚼年少时的悲苦记忆。萧乾笔下的苦难儿童总与同样凄惨的母亲、姐姐等柔弱女性相互依偎,而强有力父亲角色的空缺不仅符合萧乾的现实生活境遇,也蕴含着萧乾对孱弱国家地位的无奈。
“无家”与“弱国”的叠加加重了萧乾内心需要倾泄的苦闷,以文学治疗心灵创伤的写作目的使得萧乾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郁达夫式“自叙传”特色。他不断强调自己的“忧郁”和“病态”,苦于无法走出极端情绪——过度的积极热情和悲观厌世,时常徜徉在抒情色彩浓厚的小说中寻求心灵慰藉。小说中人物出现高度模式化倾向,环哥与母亲寄住在亲戚家的故事设置出现在《篱下》《矮檐》《昙》《落日》多篇小说中。他的小说饱含对家庭温情的浪漫想象和对富人恶霸欺压良善行为的无情揭露。面对日军铁蹄下的民族危难,萧乾一直苦恼于如何将高度饱满的个人情感与对国家大事的间接再现进行更好融合,1933年底他对巴金的靠拢是他为内心矛盾寻找出路的征兆。他接受巴金的建议,调整写作路径,希望走出个人“小圈子”,进入人生“大圈子”。然而,对现实的极度失望使得他不得不暂时遁入虚无的“梦之谷”,渲染了化名为“萧若萍”的他在遥远南国避难时邂逅并痛失一场惊心动魄爱情的真实经历。隐没于国难阴影之下的诗意世界无法持久,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萧乾这一阶段的文学探索戛然而止。
旅英七载,“弃文从闻”
1939年,时任香港《大公报·文艺》负责人的萧乾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这也是老舍曾经任教的地方),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此后,工作与人事的变动、新闻事业逐渐获得的关注,加上理性层面的文学救国论和感性层面的主观内倾创作的抵牾,最终导致他彻底告别小说写作,专事新闻记者工作。1942年夏,他辞去教职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浓厚的心理小说创作与研究氛围中,他重投艺术本体追求之怀抱,主攻英国心理派小说,这一选择和他早年的文学旨趣是相符的。而当他认识到这些意识流作品“脱离了血肉的人生,而变为抽象、形式化、纯智巧的文学游戏了”(李辉《浪迹天涯——萧乾传》),又毅然放弃学业,全身心投入记者工作。
1944年后,萧乾以战地记者身份亲历诺曼底登陆、挺进莱茵河、联合国成立大会、英国大选、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等重要历史时刻,写下《进军莱茵》《美国印象》《南德的暮秋》等通讯。1939-1940年间的“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也为人称道。在《银风筝下的伦敦》中,他写道:“一个妇人由坍塌的房屋底下被拖出来了,她一直等到得悉自己那四岁的孩子安然无恙才断的气,把悲哀托给了从军队赶回的丈夫。在同一天,他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爹娘同兄弟,怀抱着那咧嘴哭的孩子。”他将同情民生疾苦的人道主义情怀与重视生活细节的文学视角凝结为真实而犀利的白描笔法,写出“有血有肉”的新闻报道。空袭下受难的“活宝”英国家畜,战争中慷慨、幽默、乐观的伦敦民众,六年欧战之后急需向中国亲人报平安的柏林留学生……聚焦民生、以小见大的选材,加上简洁冷静的新闻式语言与想象和激情兼具的文学式语言,使得他的采写摆脱了概念化报道写作的窠臼,鲜活而生动地再现了战争背景下的社会广阔画面与普通底层民众。用萧乾的话说,报告文学(新闻报道)就是“鼓面上跳舞”(丁亚平《别离在新世纪之门——萧乾传》),即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最大限度发挥文艺笔法的长处。
在萧乾旅英的七年间,祖国母亲一直是他放不下的牵挂,他竭尽所能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中国抗日。“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我梦想用我的滚烫的文字,暖一暖母亲的手脚。……而我梦魂萦绕的依然是我的贫弱的祖国。”(萧乾《我的年轮》)萧乾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经常参加丰富的“课外活动”,如辩论会、电影学会、读剧会、茶会等,伯特兰·罗素和李约瑟都常请他去吃茶。萧乾与威尔斯、艾克敦、乔治·奥威尔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交好,尤其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其以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的画家姐姐瓦妮莎·贝尔为中心,集合一批多来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知识分子如E.M.福斯特、T.S.艾略特、阿瑟·韦利等,传承剑桥大学人文主义精神,可谓英国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核心力量。在他们的热情邀约下,萧乾进行了介绍现代中国的一次次演讲,振臂呼唤国际同情,这些英文演讲大都被刊登在英国报纸上,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同情。
1942年《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中国成为英国的盟邦,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知识分子对片面追求科技进步行为和观念的反思,以及对东方哲学的探索热潮,致使珍珠港事件以来,英国读者想了解中国的愿望空前地强烈。萧乾1942年出版的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现代中国文学鸟瞰》(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 A Glimp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和编选集《中国而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引起很多关注。1944年,他又接连出版文集《龙须与蓝图(战后文化的思考)》(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Meditation on Post-War Culture〕)、编选集《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小说集《吐丝者》(The Spinners of Silk,或译为《蚕》)。他的这五本由相关演讲和文章合并的英文著作集中介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抗战文艺、近现代史和中华文化相关知识,被人合称“英伦五书”。萧乾一方面期冀古老中国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尽快摆脱落后地位;另一方面竭力重建现代中国形象,以修正英国人以及西方人对古董式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五本书在英国获得再版,并有多篇书评发表,《吐丝者》还于1947年在瑞士苏黎世以德文译本出版。
文坛多面手,一腔爱国情
1946年萧乾回国,在上海、香港的《大公报》撰写社论,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与新闻系教授。1948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公报》起义筹备工作和中共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中国文摘》的编辑事务。同年,他将《大公报》“红毛长谈”专栏的文章汇集出版了杂文集《红毛长谈》。该书假托一个来自拉脱维亚的流亡商人、红毛记者“塔塔木林”来观察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对当时中国人已经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予以深刻剖析,极尽滑稽和揶揄之能事,展现了萧乾讽刺杂文写作的卓越才能。
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萧乾历任英文《人民中国》杂志副总编辑、《译文》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等。破旧立新的历史变革使得萧乾心情振奋,写下多篇特写,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成立前,萧乾就写下诸多旅行通讯,那时的他,一心为了“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萧乾《人生采访》)。萧乾在国内遍访归绥、鲁西、湘黔、滇缅、岭南、海陲等地,在国外足迹遍布西欧、美洲和南洋等区域,游历中的所见所感激发他创作了多篇反映社会现实的佳作。萧乾在大学暑假期间,乘坐货车在平绥线上考察塞外风貌,写下他生平第一篇报告文学《平绥道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把题目改为《平绥琐记》)。他在采访过鲁西的黄河决堤大水灾后,写出《鲁西流民图》等一批反映民生疾苦的特写名篇。在他的诸多通讯中,《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是广为传颂的佳作,山水通讯《雁荡行》等别具特色,他的西欧战场报道也最为世人所熟知。为一块馍馍你争我抢的难民、在赈灾中中饱私囊的官员、壮丁们用白骨血肉铺成的滇缅路……如果说,过去的黑暗现实驱使萧乾用如椽巨笔歌民生之哀哭,新中国的蓬勃气象则激励他真心为之欢唱。
1951年初,萧乾参加了湖南省岳阳县的土地改革。很快,他的长篇特写《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描摹了中国共产党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撑起农民腰板的社会画面,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笔推荐。数万字的长篇英文通讯《土地回老家》在英文版《人民中国》连载,很快被译为11种外文,以土改中的活力中国有力回击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新生政权的偏见。1956年,萧乾随作协访问团到内蒙古进行参观游览,这也是他生平第三次来到内蒙古,受发生着巨变的新时代的感召和蒙古族身份的影响,萧乾挥毫写下《万里赶羊》《草原即景》《时代在草原上飞跃》,歌颂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的翻天巨变。
1989年,鉴于萧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卓越贡献,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号召联合全国32家文史馆,共同编纂了《新编文史笔记丛书》。这套丛书共50册,六千余篇,五百多万字,汇编全国两千多位文史馆馆员和馆外的耆宿名流亲闻、亲见、亲历的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的典故轶事,对补足正史具有重要意义。他还对各地请他写序的来信一律“有求必应”,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等书写下大量序言。1990年初,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八十高龄的萧乾和妻子文洁若投身《尤利西斯》的翻译,历时四年乃成。这部译作的诞生代表了萧乾多年文学翻译事业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萧乾就不间断地从事着外文翻译工作,仅1956年就译有《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三部名著,并以译笔流畅、文字灵动著称。面对这部被誉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首”的传奇作品的挑战,在对原著的深刻理解前提下,他们的翻译尽量保留了乔伊斯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包括意识流手法和多语言混杂的特点。为方便读者理解,萧乾夫妇还撰写了厚厚的导读册和20万字左右的注释,解释其文化背景、历史典故和语言难点。《尤利西斯》的翻译作为萧乾20世纪40年代未竟“剑桥梦”的接续,在文洁若负责“信”,萧乾负责“达”“雅”的互补合作中,成就了华语世界第一个《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自称副业是“沟通土洋”的萧乾,还积极延续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旅英期间的文化交流事业,多次走出国门,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参加文化交流会议并发表演讲,介绍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以及他的文学与新闻思想。
改革开放后的晚年萧乾,以“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为座右铭,不遗余力地撰写回忆散文,进行大胆的自我解剖。代表作品有《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等长篇自传,以及《一本褪色的相册》《点滴人生》《我这两辈子》《八十自省》《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等随笔。尤其是《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以其平实文笔和真实内心袒露而广受好评,也最为萧乾所珍视,在他的力邀下由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译为英文。该书还有汉学家丸山昇的日文译本及其他语种译本。
这,就是萧乾。萧乾称自己为“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在发表《梦之谷》之后,他告别小说探索专事新闻写作;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到手在即,他又旋即放弃,转头赶赴欧洲战场——这两次人生路向的艰难取舍,分别对应中国国内抗战全面爆发和英国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刻。他的经历与抉择,与夏志清所谓“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重合,共同谱写了国难时期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熠熠篇章。近代以降、“五四”以来的民族忧患内化在他心中,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演化为更为鲜明的“国家至上”观念和中华民族的大情怀。这也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义无反顾放弃优渥待遇回到祖国的原因所在。抗战结束后,萧乾再次回归对语言本体的追求。他不时强调,从20世纪30年代初踏文坛开始,他的最终鹄的是写小说;到了40年代,野心依然是在小说写作上。改革开放后,萧乾积极介绍并翻译意识流文学。他晚年多次表达了对审美问题尤其是对语言的关注、自己当年从事新闻事业的权宜考虑。他在采访中不时提到“我还想写一个长篇小说”,在文学自传中不止一次表达自己的真正兴趣在探讨文学语言,“我喜欢新闻这一行,但是我更爱文学创作”(萧乾《回顾我的创作道路》)。晚年萧乾的回忆录大多围绕文学展开,而较少对新闻写作进行总结。纵观萧乾早年的文学旨趣以及他于20世纪40年代和新时期对意识流等英国文艺的专注探索,萧乾赋予“新闻”以接触更广阔人生面等目的,而独留文学为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时代的变迁并未改变萧乾作为初衷的文学信念,只不过在家国危难面前,一切个人情感与偏爱均需让位于祖国的需要。
“在具有同样经历的当代知识分子当中,萧乾是最多地谈论自己的历史的人”(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倒卧”的“大鼻子”对自己的刺激被晚年萧乾多次讲述,用来解释自己1949年决定归国的缘由。虽一度经历风雨,他一再强调当年选择的无怨无悔。崇尚自由的浪漫心性融为他骨子里对文学始终如一的热爱,孤苦无依的成长经历,加上民国初年特殊时代背景下被歧视的“小鞑子”身份,使得他对国家强大的渴望格外强烈。“弱国子民”身份促使他将对母亲的依恋愈加倾注于对祖国的热爱,旅英经历将熔炼于萧乾生命深处的国家观念变得更为理性。李泽厚曾将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归纳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文坛多面手”萧乾一生对文学与文化的追求也可化约为“文学”与“新闻”的此起彼伏。对于萧乾这位“未带地图的旅人”而言,在这首壮美乐章的谱写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祖国正是牵绊他一生的原点。
值得一提的是,萧乾作为杰出的蒙古族作家,对民族故土的感情真挚深厚,萧乾遗孀文洁若将萧乾文学馆建在内蒙古大学正是对他的理解和成全。自2008年成立起,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作为国内唯一一家集萧乾文学艺术创作经历和作品收集、研究、展示为一体的文化场馆,已成为我国一处全面记录和展示萧乾文学文化和进行人文教育的重要文化场所。
[作者:云 韬,系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执行馆长,本文系“萧乾文学馆开发研究项目(10700-121007)”的阶段性成果]